《玩偶之家》中“她”的醒觉
本文转自:中国妇女报
省略,娜拉的价值在于她勇于虚构一个东说念主,不管男女,是否有权按我方的意志在世?开脱与对等从来不是极端,而是每一代东说念主都必须再行争取的来源。
《玩偶之家》中“她”的醒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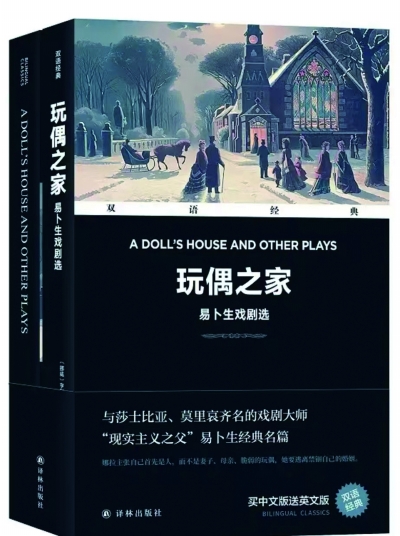
■ 班航
《玩偶之家》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于1879年的作品,2022年由译林出书社出书方中语译本。这是一部深化叩问女生运说念与社会恶疾的文体经典。书中的女主东说念主公娜拉,算作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中反叛男权社会固有不雅念的典型女性形象,其出走的抉择为作品注入了激烈的念念辨色调,深化表透露妇女解放的期间主题,既探讨了妇女在钞票阶层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问题,又通过海尔茂的形象完成了对本钱成见社会男性公民的塑造,揭露了钞票阶层的自利和毛病。
娜拉率先是阑珊个体相识的,在家庭中,她仅算作男性的隶属而存在。但在资历“伪造签名”事件之后,娜拉的自我相识便喷薄欲出,“你又叫我扈从前通常乖乖地作念你的小鸟儿,作念你的泥娃娃”,她以讲话的猛烈透顶撕开毛病的家庭生活面纱。而海尔茂在事件影响我方声誉前的魄力反差,举例危境时公然质问娜拉“毁了家庭幸福”“损伤自己名誉”,危境废除后便换上温东说念主情具,许愿“永远襄助你”,各种行为都让娜拉认清了丈夫是一个自暗里利、庸俗下贱的“假道学”,雄壮的容貌落差,迫使她再行注视我方的地位。
在对社会法律、家庭伦理、说念德标准等进行深化念念考后,娜拉决心成为寂然的东说念主而出走。她选用与家庭透顶决裂,即便要离开儿女,也不肯再作念“玩偶”一般的东说念主,此时,理性降服了理性,成为她不屈男权压迫的中枢力量。
靠近海尔茂“你在这儿很安全,我不错保护你,像保护一只鹰爪子下面就出来的小鸽子通常”的作念张作念致,她并未千里溺。海尔茂永远以傲睨一世的姿态,在甜密话语中渗入着对娜拉的截至,如书中所言:“如果男东说念主宥恕了他浑家——信得过宥恕了她,从心坎儿里宥恕了她——他心里会有一股没神色描写的好味说念”。他的毛病与娜拉所期待的“名胜”酿成显然的对比,算作家庭的撑捏,海尔茂莫得践行“我平静为你昼夜职责,我平静为你受尽清贫”的誓词,反而以“男东说念主不成为他爱的女东说念主就义掉我方的声誉”为原理逃匿遭殃。
当“名胜中的名胜”并未出现,娜拉在失望中,纰漏决定挣脱闲居管理。而当海尔茂以“女东说念主一世中最圣洁的遭殃”遮挽时,娜拉的回答非常矍铄;“来源我是一个东说念主,跟你通常的一个东说念主——至少我要学作念一个东说念主”,这时的娜拉皆备廓清,已皆备烧毁了旧的不雅念,要与往时的自我决裂,要用我方的头脑去念念考问题,回来到稠密稠密的天下中,去享受我方该领有的开脱。
恰是这些情节的灵活性与传闻性,加之娜拉身上桀敖不驯的“偶像龙套者”气质,让《玩偶之家》深受“五四”新文体作者和读者的难得。鲁迅、胡适、茅盾三位“五四”新文化通顺前驱,也分袂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对《玩偶之家》进行了解读和价值评判。
值得提防的是,易卜生并莫得叮嘱娜拉离家出走后去了那边,这是一种刻意的留白,他意外为社会问题提供门径谜底。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分解,易卜生“是在作诗,不是为社会建议问题来且代为解答”。这背后藏着一个耐东说念主寻味的遗闻,相传易卜生曾在一次饮宴上,当读者盛赞《玩偶之家》是女性解放的宣言时,易卜生却漠然回复“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兴味,我不外是在作念诗歌”。
鲁迅基于其时的社会本质,将娜拉走后的运说念预判为:“不是腐朽,即是回来”。这个预判在他的演义《伤逝》中得到呼应。《伤逝》的女主角子君受到新念念想影响,如娜拉般勇敢,挣脱旧家庭与涓生同居,却在琐碎的生活中徐徐失去对崭新事物的探索,丧失念念想的斗争性与先进性。最终再次回来家庭,印证了娜拉式出走在阑珊经济寂然与社会支捏布景下的窘境。在《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运说念如何,咱们不知所以。子君却在涓生所赐与的“委果”——无爱的东说念主间毕命了。为何子君会抑郁而终?这就在于社会念念想新故人替之间存在着卓绝漫长的跨度,子君算作一个处在旧女性与新女性之间的“中间女性”,她的结局是期间夹缝中的势必宿命。
《玩偶之家》所承载的妇女解放的主题,自其面世,便激励中西方的共同计议,且一直不息到咫尺。在西方语境中,这部作品探讨了以娜拉为代表的女性在钞票阶层家庭中的地位和生活问题。而当它传入中国,与“五四通顺”的发蒙念念潮共振,娜拉成了中国新女性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一代女性龙套封建礼教的管理。百年往时,今天的中国女性在西席、干事、法律职权等方面赢得了长足跳跃,男女对等也早已写入法律、融入环球话语。但《玩偶之家》的故事莫得隐匿,子君的窘境也仍然存在。省略,娜拉的价值在于她勇于虚构一个东说念主,不管男女,是否有权按我方的意志在世?开脱与对等从来不是极端,而是每一代东说念主都必须再行争取的来源。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中国现现代文体专科计议生)